
2025年秋天,103岁的杨振宁先生平静地告别了这个世界。消息传来,引发的不仅是对一位科学巨擘的追思,更是一种深切的、关乎未来的文化焦虑。他带走的,似乎是一个时代的最后回响,一种再也无人能复制的、对科学本质与教育真谛的通透领悟——他称之为“Taste”。

曾几何时,有识之士发出这样的慨叹:若想推动中国教育,只出一招,那便是请杨振宁先生挂帅,重组数理化教材编撰委员会。这并非仅仅源于他诺贝尔奖得主的耀眼光环,而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一部活着的科学史。我们无法想象,在当今世上,还有谁曾与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的草坪上散步交谈,曾与费米在实验室里切磋,曾与费曼就物理学的根本问题激辩,又亲眼见证了数学巨匠西蒙斯从几何大家转型为量化投资之父的传奇。他是连接那个群星璀璨的“英雄时代”与当下的唯一“活化石”。他最深切的关怀与最后的遗憾,或许都凝结于一个我们如今已甚少提及的词汇——Tas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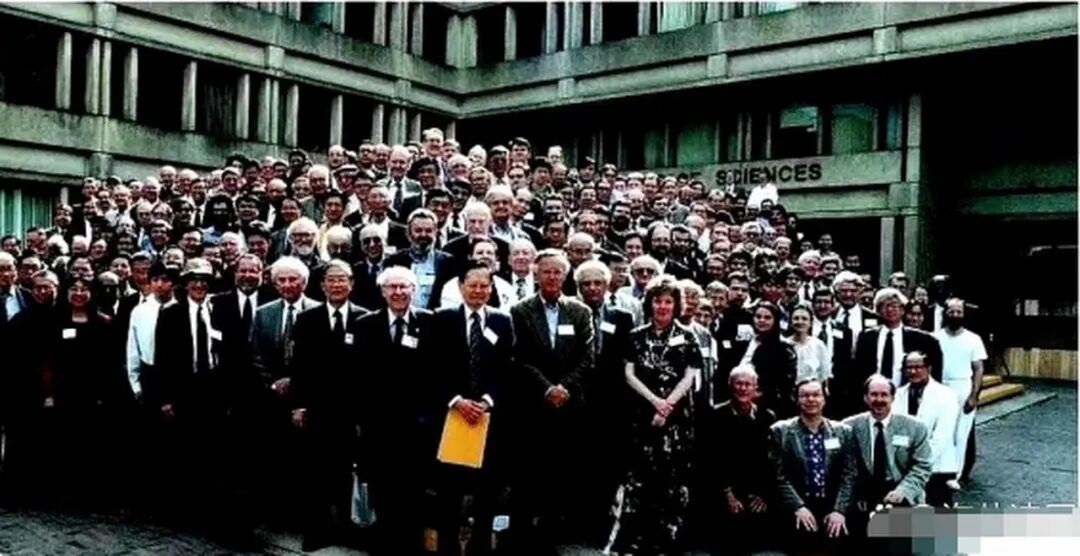
一、 何谓“Taste”?—— 超越知识的“妙”之体悟
杨振宁先生曾不止一次地谈及“Taste”的重要性。他讲述过一个令人深思的故事:他曾遇到一位年仅15岁、天赋异禀的少年。这个孩子聪明过人,能够轻松地回答杨振宁提出的数个量子力学问题,展现出惊人的记忆力和理解力。然而,当杨振宁问他:“这些量子力学的问题,哪一个你觉得是妙的?”时,少年却茫然无语,无法作答。
杨振宁对此评论道:“对他讲起来,整个量子力学就像是茫茫一片。”尽管这个少年吸收了大量知识,但他“没有发展成一个Taste”。
那么,究竟什么是“Taste”?
杨振宁对此有过精辟的阐述:“学一个东西不只是要学到一些知识,学到一些技术上面的特别的方法,而是更要对它的意义有一些了解,有一些欣赏。假如一个人在学了量子力学以后,他不觉得其中有的东西是重要的,有的东西是美妙的,有的东西是值得跟别人辩论得面红耳赤而不放手的,那我觉得他对这个东西并没有学进去。”
换言之,Taste不是知识的堆砌,而是对知识脉络的洞察;不是解题技巧的娴熟,而是对科学之美的敏锐感知;不是人云亦云的接受,而是基于深刻理解后形成的独立价值判断。它是一种高维的“鸟瞰”,能在“茫茫一片”的信息海洋中,识别出那些“石破天惊的重要连接”,感知到未知世界里那些隐秘的关联,哪怕只是这些关联的惊鸿一瞥。

他将自己一生最重要的成就,部分归功于在西南联大七年所形成的这种“Taste”。那是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于最简陋的校舍中,通过与吴大猷、王竹溪等大师的朝夕相处,通过研读最经典的文献,所培养出的“对整个物理学的判断”。这种判断力,让他知道哪些方向是充满生机、通往深邃的,哪些是繁琐芜杂、意义有限的。这背后,是从小由数学家父亲熏陶出的数学直觉,是徜徉于自然时萌发的强烈爱美之心与永不枯竭的好奇心,是西南联大不仅教授数理、也严格要求中文阅读与写作所奠定的人文底蕴。
二、 “Taste”的生成机制:人脑的“Transformer”与智慧的连接
如果我们用一个现代人工智能的术语来类比,“Taste”的形成,恰似我们每个人在构建和训练一个独属于自己的、内在的“大模型”。
我们每日汲取知识,如同为这个模型输入海量的数据。然而,一个只会死记硬背、刷题应试的“模型”,充其量只是一个高效的“记忆库”或“解题机器”。它缺乏的,正是那种能够穿透表象、洞见核心的“自注意力机制”(Self-Attention Mechanism)。
在Transformer架构中,自注意力机制允许模型在处理信息时,动态地评估并权衡不同信息单元之间的相关性,从而提取出最关键、最本质的连接,最终形成对整体语境更深层次的理解。同样,人的“Taste”也是一种高级的认知功能,它通过对知识的反复咀嚼、思辨与欣赏,能够在看似无关的概念间建立起“石破天惊的连接”。
牛顿看见苹果落地,联想到的是星月运转的宇宙规律,这是Taste;爱因斯坦追光的思想实验,最终颠覆了绝对时空观,这是Taste;杨振宁与米尔斯提出的规范场理论,将物理学中诸般基本力统一于一个极其优美的数学框架之下,这更是Taste的巅峰体现。他们不是在知识的平面上做加法,而是在认知的维度上实现了跃迁。这种跃迁,依赖于那种能够识别“妙”的神经网络连接——那是在无数平庸的、常规的连接中,闪耀着智慧光芒的、关键的通路。

因此,Taste不仅是一种审美,更是一种生产力,是原创性科学的源泉。它让学者不至于沦为文献的奴隶,而是成为思想的探险家。
三、 时代的悖论:在“硬科技”的呼喊中,我们正与“Taste”背道而驰
然而,审视我们当下的教育氛围与科技政策,一个巨大的悖论赫然显现。
一方面,“大力发展硬科技”、“从零到一的突破”成为响彻云霄的口号。社会对实用技能、短期效益的追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数理化成了一张张布满标准答案的试卷,其价值被简化为高考分数和就业前景。孩子们从很小的时候起,就被卷入无休止的刷题竞赛中,他们或许能熟练地解出复杂的微分方程,背诵出所有的物理公式,但问及“哪一个方程是美妙的?为何美妙?”时,恐怕大多会陷入如那位15岁少年般的茫然。

这正是杨振宁所担忧的:“如果没有Taste,而总是追求有用,可能很难走得远。”当我们把教育异化为一种纯粹的“有用性”训练时,我们恰恰扼杀了产生最伟大、最原始创新的土壤。因为真正的“从零到一”,从来不是基于功利计算的技术叠加,而是源于对自然深层和谐与简洁之美(Taste)的强烈信念与追寻。只重“理”之技能,而轻“文”之滋养、轻“美”之熏陶,培养出的或许是优秀的工程师,却难以孕育出有格局、有洞察力的大科学家。
另一方面,知识的爆炸性增长与学科分工的日益精细化,也使得学习者更容易陷入“茫茫一片”的困境。信息过载而智慧稀缺,工具繁多而方向迷失。在这种背景下,杨振宁所倡导的,那种能够高屋建瓴、把握学科精髓与脉络的“Taste”,显得愈发珍贵而迫切。
他仿佛一位孤独的先知,指出了通往更高境界的道路,而整个社会却在另一条看似更快捷、更实用的道路上狂奔。我们拥有了更庞大的科研队伍、更充裕的经费、更先进的设备,但为何仍时常感到“大师远去”的寂寥?或许,我们缺失的,正是那种在西南联大的茅草屋里、在战火的间隙中,依然能够被精心培育和坚守的,对知识本身那份最纯粹的热爱与鉴赏力。
四、 未竟的遗产:重编教材与“Taste”的传承
由此,我们才能更深切地理解,为何“让杨振宁当组长,重编数理化教材”的建议,会承载着如此沉重的期望。这绝非简单的知识更新,而是一场旨在重塑科学教育灵魂的尝试。
一套经由杨振宁先生之手编撰的教材,我们或可期待,它将不会仅仅是概念、公式和习题的罗列。它会在开篇就引导学生去欣赏整个物理学大厦的宏伟架构与内在和谐;它会在讲述牛顿力学时,揭示其如何体现了宇宙的对称与简洁之美;它会在介绍量子概念时,重现当年那场革命中思想的碰撞与那些“值得面红耳赤的辩论”;它会告诉学生,哪些思想是划时代的,为何它们堪称“妙”绝。

这样的教材,其目的不是培养“活字典”或“解题快枪手”,而是点燃学生心中的好奇之火,培育他们独立的科学判断力,引导他们去发现和体验探索过程中的惊奇与喜悦。它传递的不仅是“鱼”(知识)和“渔”(方法),更是“欲”(对知识的渴望与审美)——那正是Taste的种子。
遗憾的是,斯人已逝,这个构想终究成了未竟的遗愿。它象征着一种更高维度的教育理想,在当下功利主义的洪流中,显得如此曲高和寡,难以落地。
结语:安息与前行
杨振宁先生的离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他是我们身边曾真实存在的、与人类最顶尖智慧脉络直接相连的最后桥梁。他带走的,是那种在与爱因斯坦、费米、狄拉克等巨匠交往中淬炼出的、无可替代的“Taste”。

愿他安息。
但他的思想,尤其是关于“Taste”的论述,如同一座灯塔,其光芒不应随之湮灭。它是对我们这个浮躁时代的一剂清醒针。在举国上下追求科技自立自强的今天,我们或许应该暂时停下对“硬指标”的盲目追逐,静心反思:我们是否正在用最高效的方式,培养着最缺乏核心创造力的一代人?
纪念杨振宁先生,最好的方式不是空泛的颂扬,而是认真地聆听他生前的告诫,重新审视我们教育与实践的根基。如何在知识传授中注入美的感知,如何在技能训练中培植价值的判断,如何在“有用”与“无用”之间,为那些关乎长远、关乎本质的“Taste”留出生长的空间——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在巨人身影远去后,必须独自回答的紧迫课题。
我们失去的,不只是最后一位具有那种“Taste”的巨人,我们更面临着失去理解、欣赏和传承这种“Taste”的能力的危险。重拾这种能力,或许才是我们对杨振宁先生最好的告慰,也是中国科学与教育能够行稳致远、真正迈向伟大的关键所在。